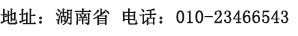凌宗亮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三级高级法官
摘要
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并不同于产品物理意义上的加工。专利产品的制造者是指专利技术方案的呈现者,即将专利技术方案在产品上予以再现的主体。既包括自行实施专利技术方案,也包括将技术方案提供给他人实施。产品外观信息仅是认定制造者的初步证据,如果被告提交证据证明侵权产品系委托他人加工,则应判断技术方案的来源方或者提供方。如果系承揽人自行负责技术方案,那么承揽人是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定作人属于侵权产品销售者,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定作人知道承揽人交付的系侵权产品,且定作人能够提供合法来源,那么定作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系定作人提供技术方案,承揽人“按图加工”,那么定作人与承揽人均属于侵权产品制造者,承揽人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的,应与定作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键词
加工承揽;侵权产品制造者;注意义务;责任认定
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如果侵权产品系侵权人自行完成的,认定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并不困难,但在加工承揽关系中,侵权产品系承揽人根据定作人的指示生产,或者系根据他人设计的技术方案加工,此时如何确定侵权产品的生产者,继而判定相应的侵权责任,司法实践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亟需明确裁判标准,为委托加工行业的发展提供行为指引和规范借鉴。
一、专利侵权产品制造者认定的司法困惑
司法实践中,权利人一般依据侵权产品上标注的商标、厂家等信息确定侵权产品的制造者,相关主体则提交委托加工合同等证据证明侵权产品并非其自己生产,而是委托他人生产。此时如何认定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实践中存在着不同观点。
(一)产品外观信息说
该观点认为可以直接依据侵权产品上标注的商标、厂家等产品外观信息确定产品的制造者,至于被告是否系委托他人生产,这属于定作人和承揽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定作人对外承担侵权责任。定作人承担责任后,可以依据合同约定再另行追偿。该观点的主要依据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批复》),即“任何将自己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产品制造者和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在上诉人北京唯信视点眼镜有限公司、华茂光学工业(厦门)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厦门璞尚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中,二审法院认为:“虽然涉案证据反映被诉侵权产品最终来源于乔凯公司,但唯信公司为授权商和委托制造者,华茂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以产品制造者的身份进行了标注,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唯信公司、华茂公司实施了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并无不当。”“被诉产品的外观设计方案或技术要求虽然来源于加工方,但这属于被告与受其委托进行贴牌加工生产的加工方之间内部的合同约定,只对贴牌委托方、加工方内部分担责任时具备法律意义。如果按照被告的观点,委托方只要能够证明其与加工方之间存在特别约定就可以免责,可能造成委托方疏于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不当减免其知识产权防范风险。权利人还需另行提起对加工方的诉讼,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权利人的讼累,不利于权利人正当维权。”
(二)共同制造说
该观点认为在加工承揽关系中,承揽人系侵权产品的加工方,当然属于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定作人基于承揽关系与加工方构成共同制造,进而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如果能够证明存在加工承揽关系,则定作人和承揽人属于侵权产品的共同制造者。在上诉人合肥安迪华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与被上诉人上海斯博汀贸易有限公司等侵害专利权纠纷中,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被控侵权产品系由斯博汀公司委托丰利公司制造完成,双方之间属于法律规定的加工承揽关系,故应认定双方共同实施了侵犯两原告涉案专利权的行为。二审法院对上述观点亦予以确认。在权利人单独起诉侵权产品委托方的情况下,该观点认为委托方即为侵权产品的生产者。在上诉人佛山市悠派厨卫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胡某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中,针对悠派公司提出其系委托生产的抗辩,法院认为:“即使被诉侵权产品是悠派公司委托他人生产,悠派公司也不能免除生产者的责任。委托生产也是生产行为,是法律意义上的生产方式之一。”
(三)技术方案提供者说
该观点认为产品上标注的信息仅是确定侵权产品制造者的初步证据,如果有相反证据证明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来自第三方,或者信息标注者并未提供技术方案,而是由承揽人自行确定技术方案,则应当认定技术方案的提供者为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在敖谦平与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委托加工专利产品的情况下,如果委托方要求加工方根据其提供的技术方案制造专利产品,或者专利产品的形成中体现了委托方提出的技术要求,则可以认定是双方共同实施了制造专利产品的行为。本案中,飞利浦公司没有向惠州和宏公司就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提供技术方案或者提出技术要求,飞利浦公司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者,其行为并不构成侵害涉案专利权。”
二、加工承揽关系中侵权产品制造者的判定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认定专利侵权产品制造者的争议,源于未能正确认识专利法意义上侵权产品制造者的本质,未区分物理意义上产品的制造和专利法意义上制造者的区别。
(一)专利法中产品制造者的界定
物理意义上产品的制造者较为容易判断,但法律意义上产品制造者的认定则要结合具体法律的规定进行理解,不同法律语境下制造者的含义可能也会存在不同。在专利法语境下,由于专利法调整和规范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实施了专利技术方案的专利产品,故专利法中产品制造者应当具有特殊的含义。根据《专利法》第十一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的规定,制造、使用、许诺销售、进口等均是实施专利的表现形式,专利权的本质在于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权利。故制造专利产品的过程本质上是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过程,实施即为再现,即将专利技术方案在具体产品上予以呈现。因此,专利法意义上产品制造者的本质为将专利技术方案在产品上予以再现的主体。专利产品制造者既可以自行再现专利技术方案,也可以授权、指示他人将特定技术方案予以再现。“将制造、使用的本义与专利方案实施的含义相结合,专利法意义上的产品制造者或方法使用者最为通俗易懂的解释,即将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产品从无到有生产出来的、将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方法步骤从头到尾实施一遍以上的。当然,从无到有应以完整的被诉侵权产品为参照,无论是将原材料制作成成品,还是将零部件组装成成品,均构成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
首先,专利产品的制造是客观的行为过程,在认定制造者时不应考虑制造者主观上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实施的系专利技术方案,也不考虑制造者的主观意图,只要将技术方案在产品上予以呈现,即为专利产品的制造者。至于制造者的主观状态影响的并非制造者的身份认定,而是其是否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有观点认为,主观上具有实施专利技术意愿的主体才是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者。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者应当对被控侵权产品已具备专利技术方案这一客观事实,具有主观上的意愿或客观上的行为。“在物理意义上总有一个主体作为实现权利要求中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主体存在,但是在规范上这一主体并不一定被评价为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者。当物理意义上从事实现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主体作为某一主体的‘手足’来实现产品的制造时,那么,物理意义上的主体就不具有规范意义上的主体地位。”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没有正确区分专利产品制造者的认定和侵权责任承担的关系,将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考虑加入到制造者认定中。一方面,这会增加专利产品认定的复杂性,导致相关认定不易被普通公众理解。例如在加工承揽关系中,承揽人明明是产品的加工人,却不认定其为制造者,会产生理解和解释上的成本和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承揽人主观上不存在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意愿,仅仅是定作人的“手足”,而不认定为制造者,那么承揽人可能因此无需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这明显不利于对专利权的保护。事实上,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者与物理意义上制造者的唯一区别在于产品制造过程中是否再现了专利技术方案,只要呈现了专利技术方案,即为专利产品的制造者。加工承揽关系中,不论专利技术方案的来源,由于承揽人客观上加工了呈现专利技术方案的产品,其应认定为专利产品的制造者,至于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是侵权责任认定应当考虑的问题。
其次,再现专利技术方案包括自行实施,也包括向他人提供专利技术方案,授权、指示、许可他人实施。如果向他人提供的技术方案构成侵权,侵权技术方案的提供者应视为侵权产品的实施者,在加工承揽关系中,可以称之为制造者。即如果定作人向承揽人提供了技术方案,承揽人只是根据该技术方案加工,即使定作人没有直接加工产品,由于其是技术方案的提供方,定作人也应视为侵权产品的制造者,此时定作人与承揽人属于侵权产品的共同制造者。在再审申请人沈阳中铁安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宁波中铁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中,宁波中铁公司的加工生产行为完全受控于哈铁减速顶中心,哈铁减速顶中心在合同中为宁波中铁公司指定了减速顶的型号及各项技术指标,并约定哈铁减速顶中心有权对宁波中铁公司的加工生产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及提出整改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哈铁减速顶中心虽没有在物理上实施制造行为,但基于其对宁波中铁公司制造行为的控制,以及最终成品标注哈铁减速顶中心专属产品型号和单位名称这一事实,应当认定哈铁减速顶中心不仅是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者,同时也是制造者。”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亦有许可侵权的规定。所谓许可侵权是指行为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允许他人实施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该制度最早可追溯至年《英国戏剧文学财产法》。该法第1条规定,作者或其代理人享有在任何地点或戏剧娱乐场所以任何方式表现或引起他人表现戏剧作品的唯一自由,并将之作为其财产。第2条规定,未经作者或所有者同意表现或引起他人表现任何此种作品属于侵权行为。因此,未经许可,擅自向他人提供专利权技术方案,进而导致专利技术方案被加工实施的,也构成专利权侵权。
(二)加工承揽关系中制造者认定的基本思路
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权利人一般都是依据产品上标注的外观信息确定产品的制造者,诉讼中被告往往抗辩其是委托他人加工,并提交相应的委托加工合同等证据。此种情形下认定侵权产品制造者的基本思路应是:产品外观信息仅是确定专利侵权产品的初步证据,如果被诉侵权人仅仅抗辩侵权产品系委托他人制造,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可以依据产品外观信息判令相关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被诉侵权人提交相反证据证明侵权产品确系委托第三方制造,此时应在征求原告意见基础上追加第三方为共同被告或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进一步审查判断侵权产品技术方案为哪一方提供。如果技术方案系定作人提供,则定作人和承揽人均应认定为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如果技术方案系承揽人自行负责,则承揽人为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定作人并不涉及技术方案的提供问题,也不涉及技术方案的再现,不属于侵权产品的制造者。
首先,产品外观信息仅仅是确定侵权产品制造者的初步证据,可以通过反证予以推翻。前述《最高法院批复》更多的系从程序或证据意义上明确产品的制造者,以方便权利人维权,并不是认定产品制造者的最终依据。在适用《最高法院批复》确定产品制造者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产品上既有商标,也有明确的生产者信息,一般应以标注的生产者为产品的制造者,不宜再以产品上所贴附商标的权利人为产品的制造者。在胡某与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其他行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上虽然标注有威力狮公司的商标、图案、英文字母及网址,但还标有尚谢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光明作为专利权人和设计人的外观设计专利号码,尚谢恩公司亦提供其与威力狮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并陈述被控侵权产品由其生产,且对产品上标注有威力狮公司的商标图案等内容作出了解释。长沙市知识产权局据此认定威力狮公司并非被控侵权产品的直接生产者,符合行政裁决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其次,有证据证明存在加工承揽关系的,确定专利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关键在于判断技术方案的提供者,即技术方案的来源。具体判断时应当审查技术方案的提供者提供的是否属于完整的专利技术方案。如果定作人仅仅是提出技术指标的要求,或者是在承揽人提供的诸多技术方案中做出最终选择,或者存在对承揽人加工过程进行监督检查,而不是技术方案来源的获取者或者提供者,均不应据此认定定作人系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在美泰利装饰公司诉钦州港务局等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中,法院认为,判断谁是承揽定作物的制造者,关键是看定作物是谁设计的,即体现的是谁的创造意志,而不是看定作物是以谁的技术和劳动所完成的,因为它是服从和服务于创作意志的。被告港务局是该承揽定作物的设计者,因而是制造者。被告丽光公司作为承包人即承揽人,其只是将被告港务局的设计图纸和选定的图案(被控侵权产品的外观设计)交由他人制作,其不是该承揽定作物铸铁栏杆(外观部分)即本案被控侵权产品的设计者,因而不是制造者。
三、制造商和销售商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本质
制造、销售专利侵权产品等均属于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均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但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存在着一定区别。如果是制造行为,则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一般应推定制造者主观上存在过错,实践中大多直接判令侵权产品制造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销售行为,销售商则可以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符合条件的销售商可以免除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对于侵权产品制造商,虽然不可能适用专利法针对销售、使用等行为人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条款,但是否一旦认定为制造商,就当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无疑问。例如,在加工承揽关系中,如果侵权技术方案系定作人提供,加工方仅仅是根据技术方案加工,虽然其客观上再现了该技术方案,与定作人都属于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应当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但是否一定构成共同侵权,进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司法实践对此似乎未予以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