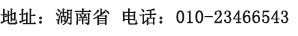作者:刘影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心特聘研究员
在如何计算符合FRAND承诺的许可费率这一问题上,从“美国微软诉摩托罗拉案”中基于假想交涉协商法(HypotheticalNegotiation)的尝试,到“华为诉IDC案”中比较协议法也可称之为自下而上方法(Bottom-upApproach)的创新;从“InreInnovatio案”中自上而下计算方法(Top-DownApproach)的初试,到“日本苹果诉三星案”中累积费率峰值(AccumulatedRateCeiling)的设定;从“美国TCL诉爱立信案”一审中对自上而下计算方法的适用,再到“英国UP诉华为案”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的结合,以及对全球费率的大胆判定,纵观全球审判实践,可以说,各国司法机构进行了大量方法论层面的探索和尝试。
迄今为止,司法实践仍未在方法论层面达成共识,给市场主体提供一个明确指引。我们看到的是,在不同案由类型、不同证据规模和不同技术样本等特定场景条件下,法院似乎在多个原则中“各取所需”地适用,“排列组合”后能够得出或高或低、或有利于SEP权利人或有利于标准实施方的费率结果,这与指导市场主体理性定价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其中,专利劫持、许可费堆叠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形成共识。鉴于,已有诸多笔墨附着于这些讨论,本文故选取一个还未被“充分开发”的视角,即可比协议法原本带有市场本色,但为何在计算FRAND许可费率过程中存在适用上的硬伤?
//一、可比协议法的适用基础和特点//
在美国,专利损害赔偿被认为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美国法院的主要计算依据是假想协商法(hypotheticalnegotiations)。该方法能够充分考虑到技术、竞争市场、法律要求以及商业惯例等会影响到合理许可费的十五个因素,也即Georgia-Pacific要素[1],这为美国法院审理损害赔偿或者FRAND费率案件提供了事实认定的基础性框架。而SEP专利组合的FRAND许可费率计算,本质上也是一个损害赔偿计算问题,因此也可以通过假想协商法这一框架进行解决。
通过假想协商法计算FRAND许可费率,是在以FRAND原则为假设前提下,结合FRAND谈判的商业实践以及不考虑禁令等胁迫性因素,双方进行理性善意的假想双边谈判,以此确定出标准必要专利的合理许可费。由于SEP专利组合具有某些需要给与限制的公权力属性并且专利权利人已经向标准化组织做出了按照FRAND原则进行许可的声明,Georgia-Pacific要素中的某些要素并不能直接适用于FRAND原则下的SEP专利许可实践,因此法院需要根据各案具体情况,对一些要素进行适应性修改。例如,在年微软诉摩托罗拉[2]以及InreInnovatio案件[3]中,美国法院均采用了修改后的假想协商法对许可费计算逻辑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目前,FRAND许可费率计算方法主要有可比协议法以及自上而下法两种。而可比协议法也可理解为是Georgia-Pacific要素中关于许可协议的考量因素,即针对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在过往许可实践中已获得的许可费数额,该许可费数额证明或倾向于证明既定涉案专利包已经达成的许可费。也就是说,可比协议参照法是将已有许可协议中的许可费作为参照,来确定当前案件的许可费率。
用于对比的许可协议可能包括同一专利权人与其他被许可人之间的许可协议、其他专利权人与同一被许可人之间的许可协议或者符合行业惯例的第三方公司的许可协议。通过许可协议来计算FRAND许可费率时,需要判断许可协议能否确定专利权人的专利价值,即过往许可协议是否可参照,这往往需要考虑过往许可协议的签订背景、过往许可协议涉及的专利包与本案专利包是否相同或者类似,判断许可协议中的标准与本案中的强制性标准是否可比。
可以认为,适用可比协议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过往许可协议与本案的专利许可争议构成可比,不同判断标准的确定可以直接影响最后合理许可费率的高低。这一点,也正是可比协议法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受到严重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
美国德州东区法院和加州中区法院分别在“HTC诉爱立信”案和“TCL诉爱立信”案适用了不同的可比协议判断标准,从而对爱立信许可报价是否FRAND产生了相左的结论,也让可比协议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再度成为FRAND争议中的焦点。
//二、“HTC诉爱立信”案的争议点所在//
年4月6日,HTC向华盛顿西区法院起诉,指控爱立信违反FRAND许可条件合同法项下的义务。年5月,华盛顿西区法院认定其对本案缺乏管辖权,故将案件移送至德州东区法院。[4]在提起诉讼的一个月之后,爱立信提出新一轮更新报价:以4G设备净售价的1%作为许可费率,且每台设备的许可费以1美元为下限、4美元为上限。爱立信前后提出的两个报价方案,HTC均拒绝接受。年8月,HTC修改其诉讼请求,请求法院确认,爱立信仍然坚持不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条件,这违反了其对ETSI做出的FRAND许可承诺,未能做到诚信谈判。年9月,爱立信提起反诉,请求法院确认其报价符合FRAND许可义务。对此,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美国德州东区法院对SEP许可费争议是否符合FRAND义务作出裁决。
在提起确认FRAND许可费率之诉前,HTC与爱立信曾于年、年和年就各自拥有的4GSEP专利组合达成交叉许可协议。在年的许可协议中,HTC同意向爱立信支付万美元固定专利许可费(lumpsum)。根据HTC对应的实际手机销量,HTC支付的许可费约每台手机2.5美元。在年的许可协议到期前,双方从年开始进行新一轮专利许可谈判。截至年底,爱立信对HTC的许可费率报价为每台终端2.5美元,HTC主张应以基带芯片的利润、而非终端设备的整体销售额作为许可费的计算基准。在年3月的谈判中,HTC提出每台4G设备0.1美元的反报价[5],这与爱立信的报价存在很大差距。HTC选择诉诸法院来解决与爱立信的FRAND许可费纠纷。
总的来看,HTC指控爱立信违反FRAND义务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许可费的计算基础。由于爱立信的报价是以4G终端设备的整体净售价、而非以基带芯片(即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SSPPU)的利润作为合理许可费的计算基础,因此爱立信的报价不符合FRAND许可义务。针对这一点,爱立信主张其与HTC相类似的公司签订的许可协议都是基于终端设备的整体净销售价,而不是基于SSPPU,因此HTC的主张不符合许可谈判的商业实践。
第二,关于可比协议的选择确定。HTC主张爱立信给予苹果、三星和华为等大型手机厂商的许可费条件明显优于爱立信给HTC的报价,这违反了FRAND原则中非歧视性的要求。针对这一点,爱立信指出,爱立信给予苹果、三星和华为等公司的许可与本案的许可纠纷相比,在许可费条款结构、专利实施人的销售地域范围以及销售市场规模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因此不能认为爱立信违反了FRAND要求。
HTC和爱立信分别就如何计算FRAND许可费向法院提交了供陪审团参考的计算方法说明。一审法院认为,SEP专利组合的合理许可费是否符合FRAND原则,需要基于特定案件的整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不存在一个确定FRAND许可费率的固定方法。因此,一审法院驳回了HTC向陪审团提供更具体的费率计算原则指引(juryinstructions)的请求。
年2月,陪审团认定HTC作为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爱立信违反了FRAND许可义务。基于陪审团的这一事实认定,法院于年5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6],确认爱立信向HTC提供的两个报价方案均符合FRAND原则,并认定爱立信已经履行了FRAND许可义务。HTC不服,于年6月向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年8月,二审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7]
//三、“HTC诉爱立信”案与“TCL诉爱立信”案的比较视角//
(一)“TCL诉爱立信”案中可比协议的确定
年3月,美国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对TCL与爱立信之间的FRAND许可费争议作出了一审判决[8],尽管本案最终采用了自上而下计算方法,但一审法院对于可比协议法也进行了完整论述。值得注意的是,TCL案的一审判决是法官审理(benchtrail)作出的,这个判决最后被二审法院推翻。[9]具体理由是,二审法院认为FRAND许可费计算本质上是一个损害赔偿问题,这在美国法传统下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因此爱立信有权就这一事实问题申请陪审团审理,一审判决在审理程序上存在瑕疵,最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虽然TCL案由于程序性问题被发回重审,但这不影响我们研究美国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在FRAND费率计算上的观点和价值取向。
在TCL案中,法官认为,与TCL和爱立信之间的许可费纠纷构成可比的过往许可协议主要包括爱立信与苹果在年签署的许可协议、爱立信与三星在年签署的许可协议、爱立信与华为在年签署的许可协议、爱立信与LG在年签署的许可协议、爱立信与HTC在年签署的许可协议以及爱立信与ZTE在年签署的许可协议。
TCL案法官在判断是否构成可比协议的过程中,主要是从竞争法的角度出发,认为ETSI成立目的是促进市场上不同公司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为了保护新兴公司可以有效参与竞争。如果将苹果以及三星等头部厂家排除在可比协议之外,这会进一步提升这些头部厂家的市场竞争力。另外,如果允许爱立信狭窄地定义类似地位的公司,这会使得FRAND原则中的非歧视这一法律侧面被架空。而在过去几十年里移动终端市场变化非常剧烈,因此可比协议的公司(即类似地位公司)的范围应当采取一个广泛的视角才更合理。具体而言,公司的地域范围以及销量等因素都是确定类似地位公司的因素,但是公司商业上是否足够成功、品牌的受认可度以及是否运用了独特的app商店对于确定可比协议的公司是没有意义的。基于此,法院最终认为,苹果和三星与TCL构成类似地位公司。
另一方面,法院认为Karbonn以及酷派与TCL不能构成本案中的类似地位公司,这要是因为Karbonn以及酷派的主要市场都是其品牌的所在国,即印度以及中国的本地市场(localking),而苹果、三星、华为、LG、HTC与ZTE的市场都是全球市场,而本案当事人TCL的市场也是全球性的,因此加州法院认为,Karbonn以及酷派与爱立信之间许可协议并不能作为爱立信与TCL争议的可比协议。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对于HTC,TCL案的法官认为尽管HTC的销量排在前十名之外,但仍然与苹果、三星或者华为等公司一样,都可以作为与TCL类似地位的公司。[10]
(二)“HTC诉爱立信”案中可比协议的确定
与比较丰富的TCL案判决书形成对比的是,HTC案由于是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公开渠道我们只能看到一份法官在陪审团判决基础上作出的事实和法律判决(memorandumoffindingoffactandconclusionoflaw)。而在庭审中,HTC主张,根据爱立信与苹果、三星、华为、LG之间的协议以及爱立信给TCL和ZTE的报价看,爱立信对HTC公司构成了歧视。作为回应,爱立信认为HTC提出的这些公司都是规模较大的厂家,这些厂家通常支付了客观的预付款,与按实际量支付许可费模式(runningroyalty)的许可协议并不相同。另外,爱立信也认为HTC提出的这些公司中的一部分,与HTC相比在销售的地理区域上存在很大不同,不能构成可比协议。
在许可协议的结构上,法院认为爱立信与其他实施人的许可都是交叉形式的,一些实施人可以通过交叉许可拿到一些抵扣,而HTC在本案之前都是将自身的专利免费许可给爱立信,这也证明了HTC自身的专利价值很低。
根据HTC判决书的有限内容可以推测出,HTC案陪审团认为可以构成可比协议的实施人可能是BLU、Coolpad、Doro、Fujitsu、Kyocera、Panasonic、Sharp、Sony这八家。这些公司的销量普遍不高,在专利许可协议谈判中很难拿到一些比价有利的费率,如果以这些公司作为可比协议的对象,对HTC公司是很不利的。陪审团认为,HTC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爱立信以4G设备净售价的1%作为许可费率,且每台设备的许可费以1美元为下限、4美元为上限的报价违反FRAND原则。基于此,法官在判决中认定这一费率是符合FRAND条件的。
对比来看,年TCL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爱立信4GSEP许可给TCL的FRAND费率在美国区域是0.45%,在美国之外其他区域是0.%。与TCL案时隔两年之后,HTC案中认定的FRAND费率却是TCL案费率的2.2倍以上。在技术层面上,可能由于HTC的销量降低,从而从一个全球销售的公司变成了一个本地公司。但这也仅是笔者的一个猜测。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考虑之外,背后可能也体现了美国不同地区法院对于市场主体之间的合同习惯与反垄断法对于自由竞争的保护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四、几点启示//
第一,选择适当的可比参照对象是可比协议法的关键。虽然可比协议法更多是尊重市场达成的交易,但是由于双方谈判地位、诉讼压力以及协议设计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选择不同的对象作为诉争案件主体的类似地位公司,会对案件的结果带来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构成可比较协议参考价值的内容,不仅仅是费率数值本身,还包括与确定费率相关背后的许可条件等,参照对象的适格性判断能否成为法院适用该方法时的一个固定审理程序,也有待深入探讨。总之,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FRAND原则中非歧视原则的具体内涵,尤其需要注意平衡市场交易习惯以及保护竞争等其他政策因素,以便更好地在个案中选择合适主体作为可比协议的参照对象。
第二,可比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仍需配合使用。目前国内关于FRAND许可费率案件公开的判决中,华为与IDC案[11]是采用可比协议法进行的计算,华为与康文森案[12]则是采用了自上而下法进行的FRAND费率计算。诚然,在不同类型的诉讼案件中,FRAND许可费率的计算目的并不相同,相应地,在FRAND许可费率计算上,不同法域采用的具体方法也不相同。业界苦苦寻觅的,能够普遍适用于不同案件类型、不同证据规模以及不同技术领域的FRAND许可费率计算公式,也许原本就带有理想主义色彩。鉴于产品复杂度、技术集成度越来越高,由此产生的专利费堆叠问题显然不容忽视,因此笔者目前倾向于认为能综合使用两种方法,既考虑到技术贡献,也考虑到交易习惯,从而在保护创新与鼓励产业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第三,实施人需加强自身专利积累并争取合理对价。正如“HTC诉爱立信”案中所体现的,如果一个实施人自身专利实力较弱,或者在交叉许可协议中没有能够充分体现出自身专利的反向许可价值,这对后续许可谈判会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实施方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关键领域的专利积累,以便在交叉许可谈判中获得较大的许可费谈判筹码。
第四,需要为披露可比协议及保护企业商业秘密提供制度性保障。商业环境下的许可协议通常会以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为由,因此不能在许可谈判中被自由地披露给第三人(许可人、被许可人各自签署的其他许可协议均面临类似的约束),而各司法辖区对于证据披露的要求并不尽相同,这也增加了获得适当的可比许可协议的难度,或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例如,如何在非诉时能做最小化的信息披露给非合同方的利益第三方?是否有义务披露所有协议?披露的协议是否为实际履行的真实协议?企业法务在何种条件下可接触此类涉第三方的保密许可协议?接触此类涉密许可信息的人员是否需承担额外的保密义务?上述与披露可比协议有关的程序问题仍待解决,这也间接导致了可比协议的适用仍会是“casebycase”,因此有必要为披露可比协议及保护企业商业秘密提供包括程序保障在内的全面制度保障,为适用可比较协议法铺平道路。
注释:
1.GEORGIA-PACIFICCorporationv.UNITEDSTATESPLYWOODCorporation,案号:F.Supp.,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
2.MicrosoftCorporationv.MotorolaInc.,etal,案号:C10-JLR,美国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
3.InreInnovatioIPventuresLLC,案号:No.11C,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
4.HTCCORPORATIONv.TELEFONAKTIEBOLAGETLMetal,案号:6:18-cv--JRG,美国德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以下简称HTC案或者HTC诉爱立信案。
5.HTCCORPORATIONv.TELEFONAKTIEBOLAGETLMetal,案号:19-,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6.HTCCORPORATIONv.TELEFONAKTIEBOLAGETLMetal,案号:6:18-cv--JRG,美国德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
7.HTCCORPORATIONv.TELEFONAKTIEBOLAGETLMetal,案号:19-,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8.TCLCommun.Tech.Holdings,Ltd.v.TelefonaktiebolagetLMEricsson,案号:SACV14-JVS(DFMx),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
9.TCLCommun.Tech.Holdings,Ltd.v.TelefonaktiebolagetLMEricsson,案号:-,-,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10.TCLCommun.Tech.Holdings,Ltd.v.TelefonaktiebolagetLMEricsson,案号:SACV14-JVS(DFMx),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第60页。
11.参见()粤高法民三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
12.参见()苏01民初、、号民事判决书。